票证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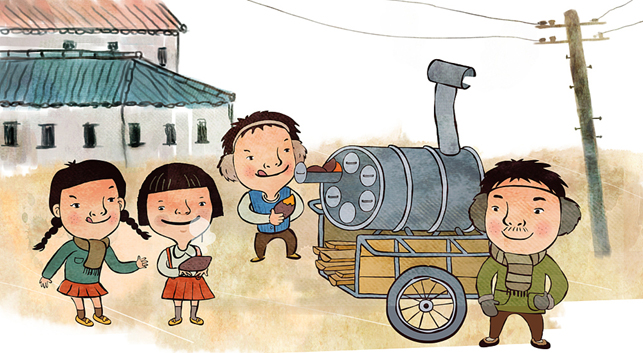
1984年上海牌手表(左),2016年上海牌手表(右)
购烟券
居民副食证
食油购买证
购粮卡
商品供应证
自行车购车证

粮票

收音机,也叫“话匣子”
票证记忆
■ 图文/于洁
周末,帮岳父收拾家,在一个破旧的箱子里发现了许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粮票、副食号、购粮票、自行车票等各类的票证,老岳父要撕掉,我连忙拦住说:“这可是宝贝,给我,我收着。”90后的儿子看着奇怪,问:这些是干什么用的?
赶上了好时代,不愁吃不愁穿,在蜜罐子里长大的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孩子们,怎么知道这些布票粮票副食票,在那个年代,就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啊!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在经济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挫折。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品供应匮乏,国家为了保持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凭证凭票凭券的计划供应,即票证制度,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对稳定市场和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发挥了积极作用。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尤其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票证以其特殊身份,伴随着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需求,没有票证真是寸步难行,在某些时候,钞票还没有票证管用,因此人们将票证称之为“第二货币”,视之为老百姓的“命根子。”
记得小时候,爸爸常年上山下乡,妈妈在副食商店工作,忙的很,经常加班加点。弟弟送了幼儿园,我和妹妹上小学,回到家里,我和妹妹就自己做饭,玉米面糊糊、稀饭不在话下,想吃馒头就得去买了,我常常在下学后揣着妈妈给的2斤粮票2毛5分钱,到饭店排队买馒头,那时候,一个人最多只可以买4斤,有的饭店为了扩大营业额,还要搭车卖玉米面窝头或者粉条汤,一人一份,只要2分钱,你不想买都不行。
记得有一次,排队到我时,只剩下不到4斤的馒头了,排在我后面的一位阿姨突然推了我一把,向售货员说:“他是插队的,没有排队!不要卖给他!”
当时我脑袋“嗡”地一声,就蒙了,结结巴巴地反驳她,但是,排在她后面的人和售货员都附和着说我没有排队,粗暴的剥夺了幼小的我买馒头的权利。这天中午,我哭着回到了家。没有了馒头做干粮,我和妹妹只有喝玉米面糊糊了。
晚上,妈妈回家后,我缠着妈妈教我发面蒸馒头,第二天早晨,吃着放多了碱面而发黄的馒头,我很骄傲!后来,不到10岁的我又陆陆续续学会了烙烙饼、擀面条、包包子、包饺子,炒菜……
妈妈在副食商店当主任,但是工作时她总不在办公室坐着,而是在店里和大家一起忙碌,调味组、副食组、水果组时常有她的身影,她待得最多的是肉案,这里最忙,但是她最喜欢在这里忙碌,搬肉、剔骨、卖肉,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这里也是可以得到实惠的,剔的干干净净没有肉的棒子骨或是没有了多少肉的排骨是可以优先卖给自己人的,这个可以不要“肉号”,1毛6分一斤,拿回家,把棒子骨剁开,大锅里加葱姜蒜大料等调料,大火烧开后,把火封好,一晚上的慢炖,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啃骨头,用骨头汤泡馒头吃了,而且啃完的骨头还可以卖给收破烂的,一斤可以卖8分钱,得到的钱我们兄妹可以去买冰棍或者大白兔糖。
优惠的待遇也是要有付出的。每月的月初,妈妈会拿回来一大兜的“肉票”,我和妹妹就会很自觉地到面缸里挖些白面出来,去火炉子上“打浆糊”,然后坐在小桌前,和妈妈一起,把肉票一张张整理好,细细的贴在废报纸或者麻纸上,这些整理好的肉票是要上缴的。每个月,都要整理一次,肉票的数量要和当月买出去的猪肉量对得上才行,妈妈告诉我们:“账实要符,不能多也不能少,工作就要认认真真,不能给‘公家’亏损了”。
所以,小小的我,很为“上班”着迷,每到节假日,就跑去妈妈单位“帮忙”,像大人一样,帮着卖货。尤其是国庆的时候,妈妈单位组织到公园售货,我是一定要去“帮忙”的。看着我在公园长廊的“柜台”里忙碌,真是羡慕嫉妒恨了前来买糖果的我的同学们!
儿时的我们这一代,赶上了“十年动乱”,经济倒退的同时,粮油副食品及各类商品严重紧缺,所以,每个家庭都把各种票证看成命根子,看得很紧。虽然政府部门规定粮票布票不能当现金流通,但是还是有人在悄悄地用小食品引诱小孩子们偷出家里的粮票布票去换一酒杯的瓜子花生,或者是几颗“大白兔”。当然,丢失粮票布票的当天晚上,大院里就会时不时的响起我的小伙伴们的“鬼哭狼嚎”。我是不屑参与“偷窃”家里粮票布票的,有个在商业部门工作的妈妈,这些小食品是吸引不了我的。可是,我也在一个晚上,参加进了“鬼哭狼嚎”的行列。因为我浪费了全家一个月的“鸡蛋号”买来的一斤鸡蛋!
听妈妈说,在我之前,应该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都早早的没有等到月份就没有了,而我也是在不足月时就很幸运的降生了。先天不足的我因此备受家人爱护,家里只要有了鸡蛋,就成了我的专利,所以我对鸡蛋是很偏爱的,宁可食无菜,不可食无蛋。有一次,我看到同学拿着家里母鸡刚下的鸡蛋上面敲一个小洞、下面敲一个小洞,放到嘴边一吸溜,就进了肚子里。我羡慕的很,就跑回家里拿了颗鸡蛋学着喝,结果喝上瘾了,连着两天喝了七、八颗生鸡蛋。鸡蛋壳没有地方处理,就塞到了火炉子底下,因为只顾自己而没有给弟弟喝生鸡蛋,妈妈回家后,不到两岁的弟弟用实际行动告了我的黑状。他用火钩子把藏在火炉子下的鸡蛋壳都给扒拉了出来。结果,我“悲剧”了。后续是,我们家厨房旁,多了个鸡窝,同时也多了几只鸡。我和弟弟妹妹也就多了一个“饲养员”的职务。
对布票的感觉始终不太强,大概因为家里孩子相对少,妈妈单位又有工作服穿,布票的消耗量小,所以每到过年我们都能穿上或蓝或绿的新衣裳,妹妹还能有花裙子花袄穿,不到冬天来临,奶奶(我小时候的保姆)就给我们三兄妹准备好了从头到脚的棉衣棉裤绵鞋棉帽,所以小时候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小孩子穿大孩子衣服的“传统”,直到我上高中,还在穿奶奶亲手缝制的棉衣棉裤。而过年的新衣服,最早时是去商店买成衣的,但是这样太浪费布票了,于是妈妈便向奶奶和邻居嬢嬢学习裁缝手艺,学着给我们兄妹做衣服。记得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妈妈向公司领导求助,搞来了一张缝纫机票,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其代价是,单位分配给爸爸的飞鸽自行车票换给了妈妈公司的领导,好在那些年爸爸总是下乡或者出差,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用自行车的机会不多,妈妈也有一辆凤凰二八自行车,够用了。
快过年的时候,缝纫机买回来了,整个大院都轰动了,邻居阿姨们纷纷登门向妈妈借缝纫机用,为了加快给孩子们做新衣服。甚至有阿姨提出给妈妈几尺布票,插队先来做衣服。妈妈拒绝了,都是邻居,还是一个大单位的,不可以占这个便宜。妈妈提议大家协助一起干活,共同给孩子们做衣服,也可以节约时间。这样,工作忙的妈妈又可以“偷懒”了,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妈妈始终没有学会做衣服,她学裁缝的成果就是给她自己和我妹妹做了两件连衣裙。精明的奶奶虽然不会踏缝纫机,但是她会做很多手工活,裁剪衣服留下的布头被她收集起来,小块的布头给我和小伙伴们做了许多的沙包,大部分布头则被她打了许多浆糊,粘成布片,纳了鞋底,分给了大院的邻居们,有些不好做鞋底的布头也难不住奶奶,她把它们抹上浆糊缠卷起来,做成了门帘。
对粮票重要性有了感觉是每个月要帮着妈妈去粮店买粮,那个时候吃商品粮的市民每人每月有28斤粮,上小学的我和妹妹是18斤,随着年龄增长粮食供应也逐步增加。当弟弟出生时,我已经7岁了,记得是个大年三十儿,我在医院摸着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弟弟的小鼻子给他“擦汗”时,妈妈说了句:“这小家伙,已经挣8斤粮食了。”
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我们兄弟姐妹的长大,家里的粮食也开始出现了困难,因为河北老家连年遭灾,农民辛苦一年,分到手的只有一家20斤麦子和200斤红薯,舅舅来找妈妈求助,妈妈把多年来积攒下来的粮票买来了几百斤玉米面,交给舅舅。我们兄妹终于开始感受到了其他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不够吃时的困境。以前,虽然按照粮食分配每户家庭的粗细粮比例是只有35%的细粮,但是妈妈总是把粗粮换成细粮来给我们吃,而副食上的便利使得我们没有感觉到其他家庭的困境,如今,粮食都不够吃了,怎么可以再换着吃细粮啊!玉米面窝头、红面糊糊、包皮面成为了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主食。从小没有受过苦的我更是遭了罪。因为以前的我可是从来都跟爸爸一个待遇,只吃细粮不吃粗粮的,现在不行了,要和弟弟妹妹一样了,不但要吃粗粮,而且要带好头,不能叫苦。每次做饭要用细箩来箩陈旧的红面,看着箩出来的肉虫,直泛恶心,但是,还得和面擀面,还得吃下去。我的饭量越来越小,胖小子也变成了瘦小子,还被同学给起了个“毛猴”的外号,此时的我真想早点毕业,像书里描写的知识青年和大院里的哥哥姐姐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番。
1975年底,我们告别了居住了十二年的大院,住进了爸爸单位盖的新宿舍楼,而且是两室一厅带厨房的新楼,我们兄妹三人都有了自己的单人床,不用再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大床板上了。最高兴的是,单位奖励了爸爸一张电视机票,我们家也有了一台春笋牌电视机,虽然是12吋的黑白电视机,那也是很了不起的了!我们终于不用到别人家看人家的脸色去蹭电视看了。爸爸还买了一张带彩色的薄片,放在电视机屏幕前。嘿,也算是彩色电视机了。
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在老乡叔叔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工作,在棉织厂做销售,因为是“坐办公室”的,工资是二十元零六角,每月还有六元的奖金和六斤粮票,如果在车间,则可以挣到三十二元工资、八元奖金和十二斤粮票。但是我受不了苦,只能少挣钱了。挣钱了,经济也自由了许多,每个月交给妈妈二十元钱,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零花钱。我可以自由的去买书了,也可以不想吃食堂时,就花上四两粮票、三毛四分钱,在厂外的小饭店里奢侈地吃上两碗浇肉面了。我也可以去副食店,花上两斤粮票两块钱买上两斤点心,去看看因为白内障失明的奶奶,奶奶总是和我小时候一样,从她的宝贝匣子里摸出两个熟鸡蛋或者两块已经发硬的糕点,塞到我手里说:“给我娃自己吃,悄悄的,不要吭气”。我告诉奶奶:“我挣钱了,还有六斤粮票呢,我给奶奶买点心了,奶奶自己吃,别舍不得。”奶奶高兴地说:“我娃有福气哩,我等我娃娶媳妇哩。”可惜的是,一辈子没有工作,靠帮人看孩子做保姆的奶奶没有等到她视为亲孙子的我结婚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1983年,妈妈的单位面向职工家属招工,我考上了“铁饭碗”,可以挣三十五元钱了,虽然粮票还是六斤,但是它的功能已经开始淡化了。接着我也调到了新华书店工作,可以自由自在的看书、买书,可以去刚刚打入太原市场的陕西小吃店毫不含糊的多花五毛钱,不要粮票的吃上一碗凉皮外加两个夹肉饼(陕西肉夹馍太原叫法)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市场商品供应逐年好转,消费品市场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商品紧缺,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逐步变为买方市场。布票粮票已经不再成为家庭的紧俏证券。许多精明的农民进城,把新收的多余的粮食换给城里人,而且可以用粮票换,记得一斤粮票可以抵2毛到3毛钱,如果是全国粮票,还能多抵几分钱,尤其吸引人的是,粮票或者是陈粮可以换到以前只有南方人可以在粮店买到的大米,而且买粮不一定要去粮店了。走街串巷的小商人也逐渐多了,布票、粮票可以换到铝锅、铝盆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经意间,所有的票证突然不见了。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为吃穿发愁了。现如今不要说大超市大商场的琳琅满目了,吃粗粮也成改善生活了,不要说电话机了,手机、电脑都一人几台了,不要说半导体收音机了,电视机都几十吋的超薄大镜面带3D4K了。自行车都成健身器材了,手表、金银都不爱戴改戴木头手串了,汽车都差不多一家一辆了。返回头看看这曾经使用了四十年的票证,想想因为它曾经发生过的哭哭笑笑的故事,怎不叫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呢。(山西省分行)

